
摘要:张栻是南宋湖湘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方面通过其父张浚而承接忠孝之学以及焦定易学为主的蜀学,另一方面独得胡宏之学,主教于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将胡氏父子所传之湖湘学派发扬光大。张栻待人以诚,与浙学陈傅良和闽学朱熹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前者曾问学于张栻,后讲学于岳麓书院,使得胡张以来的功利之学真正形成传统;后者与张栻同辈论交、相互启益,推动了闽学和湖湘学的发展。此后,随着朱熹地位的提升以及真德秀、魏了翁、张忠恕、张庶、陈钢、杨茂元、陈论等人的弘扬,他本人及其闽学对湘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终造就了湘学的朱张传统。
关键词:张栻;胡宏;朱熹;陈傅良;湖湘学;学脉检视
张栻(1133-1180),原字敬夫,后因避讳而改字钦夫,又字乐斋,自号南轩,谥宣,后世称张宣公。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生于阆州(今四川阆中),后随父辗转多地,绍兴三十一年(1161)方才定居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城南之妙高峰,张氏父子建立城南书院,张栻除了在城南书院讲学,还因主教于岳麓书院而著名,对于湖湘学脉有着深远的影响。关于张栻之学,朱熹(1130-1200)曾有一个总结:
孟子没,而义利之说不明于天下。中间董相仲舒、诸葛武侯、两程先生屡发明之,而世之学者莫之能信,……爰自国家南渡以来,乃有丞相魏国张忠献公唱明大义以断国论,侍读南阳胡文定公诵说遗经以开圣学,其托于空言、见于行事虽若不同,而于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则皆有所谓千载而一辙者。若近故荆州牧张侯敬夫者,则又忠献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门人也。自其幼壮,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传。既又讲于五峰之门,以会其归,则其所以默契于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独其见于论说,则义利之间,毫厘之辨,盖有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诸事业,则凡宏纲大用、巨细显微,莫不洞然于胸次,而无一毫功利之杂。[1]
在朱熹看来,张栻之学既有家学,又有师承,远则承接董仲舒(前179-前104)、诸葛亮(18-234)以及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近接张浚(1097—1164)以及胡安国(1074-1138)、胡宏(1102-1161)父子,故得忠孝之传,而尤龂龂于义利之辨,从其一生之为学、为官来说,这些说法也是符合事实的。[2]然而朱熹并未注意到,张栻还与浙学的代表人物薛季宣(1134-1173))和陈傅良(1137-1203)的有所交往,当在功利之学上有所呼应。还有朱熹也曾提及陈傅良在湖南任职三年,对张栻弟子影响颇多,使得“胡张”以来的功利之学真正形成传统。朱熹两度讲学岳麓,前者与张栻进行“朱张会讲”,后者则在知潭州之际,编定张栻文集并再度讲学,后来随着朱熹学术地位的升格,在其影响之下又形成了湖湘学脉之中更加明晰伊洛正传的“朱张”传统。事实上,以讲明义利、功利经世之学的“胡张”传统,在“朱张”传统之中也一直隐伏着,他们共同推动湖湘学脉在后世的演进,从“胡张”到“朱张”学脉转换、显隐的过程,除了胡宏与朱熹的影响之外,又还有陈傅良的冲击,对于其中各种学术派系分别如何发挥作用,尚有必要再多作探究。[3]

『一、“胡张”传统之由来』
说到张栻的学术渊源,最为重要的自然还是师事于胡宏而传承胡氏父子所开创的湖湘学派,通过胡氏父子张栻也对二程洛学有所传承。此外,张栻本为蜀人,在其家学渊源之中也有蜀学的一些因素。
张栻的父亲张浚为南宋“中兴”名相,张浚,字德远,学者称紫岩先生,谥忠献,赠太师,封魏国公,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川陕宣抚处置使、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等职,后人辑有《张魏公集》。张浚曾师从谯定和苏元老。苏元老(1078—1124),字子廷,眉州(四川眉山)人,曾受苏轼、苏辙兄弟的族孙,与苏氏兄弟有书信往来。谯定和苏元老也受当时蜀学的影响,带有较重的佛禅气息,因此张浚之学也有“惑于禅宗”之讥。张浚对张栻的学术影响,据记载较为重要的当是传自谯定的《易》学,因为谯定也师事于二程,故其《易》学也当有着洛学的因素。程颐-谯定-张浚-张栻,这是张栻传承洛学的学脉之一。朱熹也说到,张浚在连州之时,“日夕读《易》,精思大旨,述之于编,亲教授其子栻。”[4]张浚影响张栻最深的应当还是其忠孝精神,张浚在临终之际曾对张栻说:“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归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5]《宋史》之张栻传说:“自幼学,所教莫非仁义忠孝之实。”[6]朱熹在《神道碑》中也说:“生有异质,颖悟夙成,忠献公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7]朱熹另外还特别强调;“已得夫忠孝之传,既又讲于五峰之门,以会其归,则其所以默契于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8]也就是说,朱熹最为肯定的就是张栻通过张浚而得“忠孝之传”,而使得张栻真正接续纯正的儒家学脉,则还是来自胡宏的教诲。
除了家学之外,在师事胡宏之前,张栻还曾受学于刘芮与王大宝。绍兴十一年(1141)张浚乞祠寓居长沙,张栻也随之来到潭州,在此期间,张栻兄弟曾师从于刘芮,《宋元学案》中说:“张魏公卜居长沙之二水,授先生室,宣公兄弟严事之。”[9]刘芮(1108—1178),字子驹,号顺宁,先世为东平(今属山东)人,后徙居长沙,曾任永州司理参军、大理司直、国子监丞、湖南提刑。“学于孙奇甫,其后游尹和靖、胡文定之门,所造粹然”,故追究其师承关系,其主线为:司马光-孙伟-刘安世-刘芮,[10]再加之胡安国与尹焞等人的影响。绍兴十六年(1146),张栻又随父寓居连州,师从于连州知州王大宝。王大宝(1094—1170年),又名王元龟、二龟,海阳(今广东潮安)人,早年即入太学,建炎二年(1128南宋)进士 ,历任南雄州教授、枢密院计议 、差监登闻鼓院等。王大宝知连州时,张浚正好谪居于此,“张魏公先是州,即命其子敬夫从之学”[11],王大宝的师承关系则是:邵雍-邵伯温-赵鼎-王大宝。[12]张栻受学于刘芮与王大宝之时,才十岁与十五岁,但也为其学术打下基础,使得张栻较早就得以亲近洛学等心性之学,此二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绍兴二十年(1150),张栻随父寓居永州,这一时期张栻主要从其父张浚受学。期间,张氏父子还曾返回四川,绍兴二十六年(1156),张栻祖母逝世,归葬于四川绵竹故里。绍兴二十九年(1159),张栻完成了《希颜录》的初稿,此书表达的是对颜回以及儒学正统的认识,虽然他自己后来说:“《希颜录》旧来所编,不甚精切,颜子气象但当玩味于《论语》中,及考究二程先生所论,则庶几得所循求矣。”[13]但是也可见当年张栻的学问已颇具气象了。后来胡宏也称许《希颜录》“足见稽考之勤”[14]。
真正奠定张栻为学规模的,则是师事于胡宏。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张浚任职湖南路,张栻随父重回潭州,城南书院之初建即在此时。是年张栻尊父命从学胡宏,张栻正式前往碧泉书院拜师胡宏,在此之前他曾有书信问学。张栻说:“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胡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巳之岁,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15]然而,胡宏收下张栻为弟子,期间也经历了一番周折。据传张栻前往衡山拜见胡宏,起初胡宏以“渠家好佛”而拒见,经曾问学于胡宏的孙正儒的转述,张栻才明白其中究竟,于是“涕泣求见,遂得湖湘之传”[16]。胡宏不愿收他,还是因为张栻从张浚所传之蜀学,几近于“好佛”。关于此事,魏了翁(1178—1237)在《跋南轩与李季允帖》之中也有记载:
南轩先生受学五峰,久而后得见,犹未与之言。泣涕而请,仅令思“忠清未得为仁”之理。盖往返数四,而后与之。前辈所以成就后学,不肯易其言如此。故得其说者,发于愤悱之余,知则真知,行则笃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谓无急于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于人者教人。[17]
胡宏为了成就张栻,不轻易传授,不急于求成,方才造就真知、笃行的人才。
张栻正式问学于碧泉书院之后,胡宏也对他十分器重,现存答复张栻问学的书信就有十多通,张栻还将自己所编的《希颜录》一书寄给胡宏请正,胡宏特作有《题张敬夫希顔录》一文,其中说:“敬夫著《希颜录》,有志于道。大哉志乎!”[18]。胡宏还在与孙正孺的书信中说:“敬夫特访陋居,一见直如故交,言气契合,天下之英也。见其胸中甚正且大,日进不息,不可以浅局量也。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幸甚!”[19]胡宏后来则对另一弟子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20]他希望自己的弟子们继他之后,能够承担其道学的大任,继续成为领军人物,此后果然领军的则是张栻。后来的朱熹则认为张栻“独得”胡宏之学:“敬夫说本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21]朱熹还说:“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22]黄宗羲(1610-1695)指出:“南轩受教于五峰之日浅,然自一闻五峰之说,即默体实践,孜孜勿释。又其天资明敏,其所见解,初不历阶级而得之。五峰之门,得南轩而有耀。”[23]张栻以其天资与实践的结合,“勇猛精进”与“渐渍熏陶”的结合,最终做到了胡宏的嘱托,并将此事看作终身事,且承先又启后:
此事是终身事,天地日月长久,断之以勇猛精进,持之以渐渍熏陶,升高自下,陟遐自迩,故能有常而日新,日新而有常,从容规矩,可以赞化育、参天地而不过也。[24]
张栻曾将胡宏之言在与他自己弟子的书信中也有提及,并说:“诚至言哉!”[25]可见其极其看重视,似可视为湖湘学派的“传灯”之言。后来的张栻果然不负胡宏之教诲,主教于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将胡氏父子所传之湖湘学派发扬光大。岳麓、城南二书院成为道学的重镇,湖湘一带的学子云集于此,湖湘学派在此期间也达到一个高峰。
张栻之学初具规模之后,还在与朱熹等人的交游以及为官、为学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完善起来。隆兴元年(1163),张栻三十一岁,以荫补官,辟为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此时张浚任枢密使,率师北伐。张栻“以藐然年少周旋其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26]。也就在这一年,张栻与朱熹首次相见。第二年,张浚因北伐失利被免职,行至江西余干去世,张栻护丧归葬衡山,此时朱熹曾登舟哭之并送至丰城下船,以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互为论学之密友。
乾道元年(1165),朱熹的好友、时任湖南安抚使的刘珙,属州学教授邵颖修复岳麓书院,延聘胡宏弟子彪居正为山长,张栻担任主教。朱熹后来在为刘珙写的《行状》里说:“潭州故有岳麓书院,……公一新之,养士数十人,延礼修士彪君居正使为之长,而属其友广汉张侯栻敬夫时往游焉。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学者于公私义利之前,闻者风云。”[27]张栻在给朱熹的书信中也说“岳麓书院迩来却渐成次第”,因此后来才有朱张长沙之会讲。乾道二年(l166)十一月,张栻作有《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其中就提出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办学宗旨:
乾道元年,建安刘侯珙安抚湖南,……乃属州学教授金华邵颖经纪其事,未半岁而成,大抵悉还旧规。某从多士往观焉,爱其山川之胜,堂序之严,徘徊不忍去,喟然而与之言曰: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28]
书院办学的宗旨为传播道学思想、成就既能传道又能济民的真人才,反对仅为功名利禄而学习,其中蕴含着明确的义利之辨。此时岳麓书院的办学规模,已经远超当年胡宏主持的碧泉书院,湖湘学也达到鼎盛时期。乾道三年(1167),朱熹听说张栻湖湘讲学之盛况后,带着弟子林用中、范念德等人来到潭州,这就是著名的“朱张会讲”。两人相与讲学、论辩于岳麓、城南二书院,一时听讲者甚众,为湖湘学术之大盛事。
乾道五年(1169),因为刘珙的荐举,张栻除知抚州,未上,改知严州(今浙江建德)。此时吕祖谦正好出任严州教授,于是张、吕二人相与论学。乾道七年(1171)六月,张栻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离开临安。该年十二月,回到潭州。乾道八年(1172),刘珙复知潭州,再次整修岳麓书院。一直到淳熙二年(1175),张栻都在主持岳麓与城南二书院,继续其讲学与著述。在此期间,张栻编辑并刊行了胡宏的《知言》与《五峰集》等著述,同时又对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道学家的学术有精深的钻研,曾著有《太极图说解》《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书诠释先儒之学术,此外还著有《论语解》与《孟子说》等书,对于传统经典作出自己的解释。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以及著作的完成,标志着张栻本人思想的确立与成熟。
张栻人生的最后阶段,则又是在外任官之中度过。淳熙元年(1174),张栻诏除旧职,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经略安抚广南西路。第二年赴任之后,精简州兵,汰冗补阙,广西境内顿时清平。张栻还在静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二程的“三先生祠”:“即学宫明伦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东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29]还作有《韶州濂溪周先生祠堂记》等文章,致力于道学的南传。淳熙五年(1178),因为张栻治理静江有方,乃诏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安抚本路。张栻到任后,努力整顿军政,去除贪吏,弹劾失职官员。期间,张栻还在反复修订其《论语解》与《孟子说》等著作。他还在当地修葺学校、建立祠堂,进一步推广道学。比如淳熙五年八月,张栻因事到袁州(今江西宜春),其弟张杓为知州,新建了袁州州学,于是张栻作有《袁州学记》;他还为周敦颐的故乡道州重建其祠堂而撰写了《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另有《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等。张栻后来病重,还上书孝宗说:“伏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巩丕图。臣死之日,犹生之年。”[30]其中透露出传之其父的拳拳爱国之情,以及传之胡氏父子的道学之思,全都溢于言表。淳熙七年(1180)二月,诏张栻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诏书未至,张栻因病卒于江陵官舍。噩耗传出,举国悲戚:“柩出江陵,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讣闻,上亦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静江之人哭之尤哀。”[31]张栻晚年,为确立周敦颐在湖湘学脉中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通过《论语解》与《孟子说》等著作,对于传承自胡师氏父子及其家学的湖湘学也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张栻本是蜀人,又出生于蜀地,在其学脉之中原本就有蜀学的一系,后定居于潭州并问学于胡宏,于是传承湖湘学,方成为一代宗师。[32]张栻弟子吴儆曾在祭文中说:“先生忠孝之节,世有家法,渊源之学,心契圣传。”[33]其友人杨万里则称之“名世之学,王佐之才”。[34]这些概括与朱熹的《张南轩文集序》等文所述相似。质言之,张栻之学,一方面来自其父张浚的忠孝之家法,特别体现为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使得张栻所传的儒门圣学得以纯正而精深,主要还是因为得到胡宏的传授,他与其他湖湘学者不同的则是,能在胡宏的基础上继续开拓而非固守师说。从周敦颐到胡氏父子、张氏父子,最终湖湘学脉的“胡张”传统,在张栻的书院讲学以及著作之中逐步形成,其中除了明确的义利之辨,还有建立在《知言》与《论语解》《孟子说》等著作之上的湖湘性理之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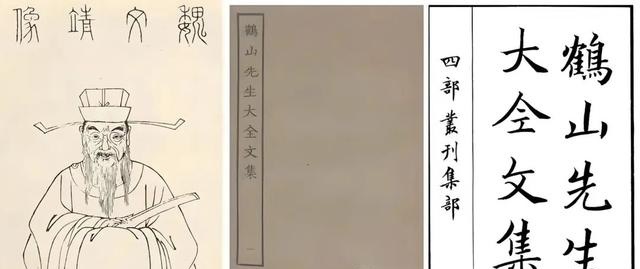
魏了翁及其论著
『二、湖湘学脉的广泛影响』
张栻是继胡氏父子之后,将湖湘学的影响推广之全国的重要学者,成为“胡张”湖湘学脉的代表人物;也正是在其影响之下,蜀中学者纷纷前来就学,又将张栻之学传回蜀中,后来影响了魏了翁(1178—1237)等一大批学者。
张栻讲学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但是说到其后学,却也颇有争议。这主要是因为朱熹的一句话:“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门人。”[35]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在张栻之后讲学于湘中,张栻的一些门人曾从陈问学,于是有人误解张栻的门人都归了陈傅良,而张栻之学则无人传承了。对此,全祖望并不认同,他说:
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然如彭忠肃公之节概,吴文定公之勋名,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实斋。谁谓张氏之后弱于朱乎?”[36]
张栻之后,其中有问学于陈傅良等人的,如胡大时、周端朝、沈有开等人。还有如这里提及的彭龟年、吴猎、游九言、刘宰、王遂等人,则依旧在承继张栻湖湘之学。另外,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之中也说:“无一人得其传。”对此,王梓材有按语说:“梨洲未及广辑岳麓、二江诸儒学案,故有是语。”[37]张栻的弟子数量多,成就也大,其发展也不在朱熹闽学之下,因此全祖望在补修《宋元学案》的时候,将张栻的门人分列两个学案,其一为《岳麓诸儒学案》,收录受学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的湖湘弟子;其二为《二江诸儒学案》,收录前来长沙受学后来大多又返回蜀中的弟子。关于张栻的弟子,《岳麓诸儒学案》记载有三十三人,则都属湖湘学派中的中坚,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吴猎(1142—1213)。吴猎,因仰慕张栻之道德文章,于乾道初年进入岳麓书院,师从张栻。张栻对吴猎也颇为器重,最终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传人之一,他后来还得到来自浙江的陈傅良的举荐,然而并不能说他转而师从于陈傅良了。
黄宗羲对张栻在湖湘学派之中的地位,有两句重要的评价:其一,“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其二,“五峰之门,得南轩而有耀。从游南轩者甚众,乃无一人得其传。”[38]黄宗羲认为张栻承继于胡宏之后,其道学造诣更为纯粹,见地高而践履实,又指出因为张栻过早去世之后,湖湘学派也就随之而式微了。关于后者,历代学人颇有争议。其实无论是在湘中,还是来自蜀中或其他地域,当年张栻都有大批的弟子传承其学术。此处先说张栻弘扬湖湘学之影响。
在张栻的主持之下,岳麓、城南二书院成为道学的重镇,湖湘学子云集于此,湖湘学派在此期间也达到一个高峰。张栻从胡宏碧泉书院回长沙之后,就在其家塾也就是后来的城南书院里讲学。城南书院是张栻的家塾,张栻曾说:“岁在戊子,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之家塾。” [39]隆兴二年(1164)八月,张浚逝世,归葬于潭州,张栻护送父灵而回到长沙,而后继续在城南书院开讲授徒。后来张栻正式主教岳麓书院之后,也经常往来于城南书院。乾道元年(1165)刘珙修复岳麓书院,次年修成后就请张栻主教于书院。乾道五年,因为刘珙的举荐张栻除知抚州,后又改知严州。乾道七年十二月,张栻重回长沙,继续主教于岳麓书院。淳熙元年(1174)张栻诏除旧职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再次离开长沙。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前后有七年之久,岳麓书院的声望与影响与日俱增,不仅湖湘学子,其他地区的学子也慕名而来,甚至有“深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40],故当时岳麓山一带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说,道林是指离书院不远的道林寺,历来书院往往不及寺庙香火鼎盛,可见当时的岳麓书院之盛况空前。
张栻除了将胡氏父子所开创的湖湘学派推至鼎盛,教授了一大批湖湘学子之外,还教授了许多重要的蜀地学子,他的学术本来就有蜀学的渊源,通过蜀地学子其学术又重新西返,在蜀地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蜀中道学的发展,促成了“蜀学再盛”。因此夏君虞先生指出:“南轩一人占住了蜀学和湖南学两席。”[41]张栻虽是蜀人,但自幼离蜀,他曾在诗中表达归隐蜀中的念头:“半生落南州,分与岷峨疏。独来荆江上,所欣近乡闾。吾乡多俊豪,杂遝来舟车。时从说情话,颇觉中怀舒……吾州得贤牧,父老想乐胥。我亦有一廛,径思归荷锄。”[42]全祖望《二江诸儒学案》收录张栻弟子,其中蜀中学者就有十四位。序录中说:
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杨浩斋、程沧州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43]
张栻讲学于长沙,蜀中学子宇文绍节(?—1213,字挺臣,四川成都人)、范仲黼(字文叔,四川成都人)、陈概(字平甫,四川普城人)等前往受学,他们将张栻之学重新传如蜀中,讲学于成都的二江之畔。受他们影响的还有陈概的友人黄裳(字文叔,普城人,学者称兼山先生)、宇文诏节的弟子程公许(字季与,一字希颖,眉山人),以及受学于张栻的杨知章(号云山老人,潼川人)之子杨子谟(字伯昌,学者称浩斋先生)等人。此外还有一批私淑张栻的学者,其中虞刚简(字仲易,一字子韶,仁寿人)、张方(字义立,学者称亨泉先生,资中人)最为著名。范仲黼、虞刚简等学者,对南宋后期蜀学的代表人物魏了翁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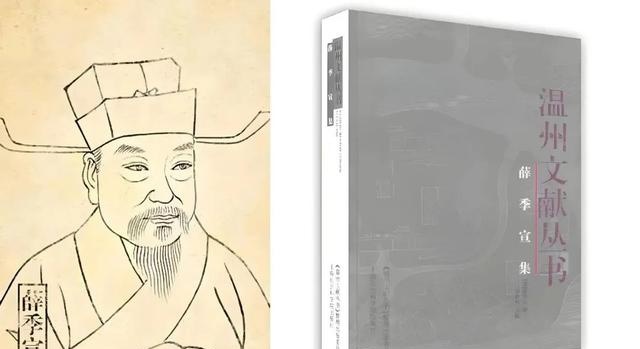
薛季宣及其论著
『三、浙学对湖湘学脉的影响』
因为吕祖谦,张栻及其后学与浙学发生了较多关联,浙学后来也影响了湖湘学,相关的重要人物则是薛季宣与陈傅良师弟二人,特别是陈傅良则有“收尽南轩门人”的说法,更有必要作一澄清。
乾道八年(1172),任职于湖州的薛季宣写信给张栻,首先提及他家与张家的渊源:“某先君右史、先伯待制皆受知于先正忠献,致位从班。”[44]他的父亲、伯父都曾受知与张栻的父亲张浚,而且他本人还曾与张浚有过一面之缘:“辛巳岁,某备县鄂陵,伏遇元戎即镇金陵,得迎拜于芦洲江步,时已昏暮,伏蒙略去贵贱等威,赐之坐席,温言慰藉,详问存没,区区感戴,鉴寐不忘。”接着又说:“闻左司以道学为诸儒唱,告猷悟主,几振吾道。”当年张栻在岳麓、城南倡导道学,在学界的影响很大,故令薛季宣非常之向往。然而造化弄人,两人终究未能见面,第二年九月,薛季宣改知常州还未到任,就在家中去世了。此前,薛季宣还在书信中向张栻请教“出处私计”,张栻在回信之中则强调了通过学校,教导当地士大夫的意义重大,他说:“某每念时事若此,良由士大夫鲜克务学之故。盖天理之微为难存,气习之偏为难矫,譬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尽,则于彼有尺寻之差矣。”[45]于是薛季宣在回信之中,提及兴办学校并邀请陈傅良到湖州一事,对此张栻也有回复:
论及学校之事,此为政之所当先也。湖学安定先生经始,当时作成人才,亦可谓盛矣。闻欲招陈君举来学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诱之读书,则义未正。今日一种士子,将先觉言语耳剽口诵,用为进取之资,转趋于薄,此极害事。若曰于程文之外,明义利之分,教导涵养,使渐知趋向,则善也。[46]
张栻反对在学校中用科举考试的程文来吸引士子,而是程文虽然也要学,但更要讲明义利之分,讲究涵养之道,从而避免浇薄的趋向。他还在另一书信中说:
某前年过霅上时,尝往拜安定先生之墓,荆棘几不通路,又墙垣颓圮,为何人所侵,势有可虑。某意谓宜专责教官掌管,令一家守之,正其封域,勿使侵犯。是时无可告语,今想自贤使君下车之后,已留意矣,谩及之。[47]
这同样是在强调学风之重要,湖州学风的倡导者,莫过于北宋的胡瑗及其苏湖教法,故而希望薛季宣在任,能够将胡瑗的墓整修一番,且安排一家人守护。相比而言,薛季宣在意的还是政事,而张栻在意的则是学术,特别是学校教育以及士大夫的人心导向。值得注意的是,张栻曾在给吕祖谦中的信中说:“士龙正欲详闻其为人,但所举两说甚偏,恐如此执害事。事功固有所当为,若曰喜事功,则喜字上㬠然有病。”[48]此信表示对于薛季宣喜谈事功之学,颇不赞许,他认为事功“固有所当为”,然“喜”则有病,其所谈“两说甚偏”,也即过于热衷事功之学,就儒门正学而言则多有偏颇了。

陈傅良及其论著
在浙学与湖湘学之间,最为关键人物其实是陈傅良。陈傅良问学于张栻,受到湖湘性理之学的影响;张栻去世之后,陈傅良又讲学于岳麓书院,张栻的弟子大多曾问学于陈傅良,湖湘学子因此而受到永嘉事功之学的影响。陈傅良早年师从于薛季宣,同时也受到吕祖谦的影响,其学术重经世致用而反对空谈性理。然而与张栻的交游,也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史》本传说:“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 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49]据陈傅良门人蔡幼学为所写陈傅良行状记载,陈傅良与张栻、吕祖谦结识当在入太学之前,当时陈傅良正师从薛季宣寄寓于晋陵(今江苏常州),拜别老师回浙:
既而薛公客晋陵,公往从之。……经年而后别去。还过都城, 始识侍讲张公栻,著作吕公祖谦。数请间,扣以为学大指,互相发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见公之晚, 是岁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学。[50]
陈傅良与吕祖谦同庚,而张栻也只比陈、吕二人大四岁,但是乾道六年(1169)的吕祖谦与张栻早就已经进入仕途,而且也因学术而闻名了,而陈傅良却尚未登第。陈傅良应当在其老师薛季宣那里听了张、吕二人之名,所以才会在经过临安之时前往拜见。
这次张、吕、陈三人会面的机会也很难得,也可以说是南宋学术史上另一大盛事。这一年吕祖谦刚刚被从严州召还,任太学博士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张栻则被从严陵召还,任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侍立官。张、吕恰好同巷而居,二人得以朝夕讲论学问。因为薛季宣的关系,他们二人与陈傅良也是一见如故,“张钦夫、吕伯恭相视遇兄弟也”[51]。会面之后,陈傅良入太学,此时当得以继续问学于张、吕二人。然而过不多久,张栻就因出知袁州而离开临安,吕祖谦也因其父去世而丁忧返乡。,陈傅良独自在临安也颇有失落之感,他在与郑伯熊(1124?—1181)的书信中说:“张侍讲方结主知,忽刺远郡。吕博士亦悼亡暂告,未果复入。年来所得师友,亦次第涣散。”[52]两年之后,陈傅良再度与张栻会面,又送别于吴兴(今浙江湖州):“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轩先生於吴兴之碧澜堂。”[53]淳熙七年(1180)张栻去世,陈傅良撰有祭文,其中说:
吁嗟先生,惟以正终。如何叹嗟,四海所同。……念昔从游,为日则浅。辱诲辱爱,辱待甚远。自我不见,常惧有靦。有来湖岭,必惠问我。对之翰墨,如在左右。蒙是曷称,罔敢违堕。[54]
从祭文可知二人之间的情谊非比寻常,特别是在陈傅良看来,张栻对他的教诲十分重要。
在张栻这边,也对陈傅良非常器重。张栻在与薛季宣的书信之中也提及与陈傅良的交往:“讲闻高谊之日久矣,近岁见吕伯恭、陈君举称说尤详,每念瞻际,以慰此心。”张栻通过陈傅良而了解到薛季宣的近况,还在另一信中谈及陈傅良入太学之事:“闻欲招陈君举来学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诱之读书,则义未正。”[55]张栻对陈傅良的教导,朱熹也曾有提及:
向来某人自钦夫处来,录得一册,将来看。问他时,他说道那时陈君举将伊川《易传》在看,检两版又问一段,检两段又问一段。钦夫他又率略,只管为他说。[56]
从这些记载来看,张栻学成较早,故对陈傅良时常提携,并指导其钻研伊洛之学。
如何定位陈傅良与张栻等人之间关系,似乎也值得讨论。全祖望在《奉临川帖子》中说:“陈止斋入太学所得于东莱、南轩为多,然两先生皆莫能以止斋为及门是也。”[57]全祖望的说法比较中肯,虽然说陈傅良得之于张栻、吕祖谦为多,陈主动问学于张、吕,但是他们三人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并不能说陈傅良师事于张、吕之中任何一人。陈傅良受到吕祖谦典章制度之学的影响,也受到张栻性理之学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对陈傅良有所促进,但并不能说很大。所以全祖望补编《宋元学案》之后,在《赵张诸儒学案》《南轩学案》《岳麓诸学案》与《东莱学案》当中,分别将陈傅良列为南轩学侣、东莱学侣。
淳熙十四年(1187)六月,陈傅良正式赴任湖南桂阳知军,淳熙十六年升任湖南提举,迁湖南转运判官,绍熙元年(1190)十月改任浙西提刑才离开湖南。陈傅良在湖南任职的三年多时间内,曾撰有《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等诗文,其政绩也得到湖湘士人的充分肯定。再就学术方面,随着张栻的去世,湖湘学派一时群龙无首,这就为在湖湘传播永嘉学提供了契机,他还与湖湘诸儒大多有广泛的交流。[58]陈傅良对湖湘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向朝廷举荐湖湘学子,其中大多为张栻的弟子;其二,讲学岳麓书院,将浙学传播于湖湘。陈傅良举荐的湖湘学子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张栻的高足、湖湘学派的中坚人物吴猎与宋文仲,当时因为担任公职,则又与陈傅良为上下级关系。
陈傅良在潭州为官时,曾讲学于岳麓书院。当时张栻已经去世多年,岳麓书院的讲学有所废弛,陈傅良讲其事功之学,使得湖南学风为之一振。之后湖湘学子多有师从他研习事功之学者,对于湖湘学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此,比陈傅良稍后才到岳麓书院讲学的朱熹曾说:“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门人,胡季随亦从之问学。”[59]这一说法太过绝对,后来引起学界众多争议,此问题在上面讨论张栻之传人的时候已经有所解释,此处不再多说。而以胡大时为代表的一批张栻在湖湘的弟子,受到陈傅良的极大影响,则是一个事实。
胡大时,字季随,号盘谷,福建崇安人。他是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之孙、胡宏之子,同时也是张栻的门人、女婿,在张栻弟子之中堪称领袖,在张栻去世之后,门人之间有议论不合则向他请益。朱熹还说:“季随在湖南颇自尊大,诸人亦多宗之。凡有议论,季随便为之判断孰是孰非。”[60]关于胡大时问学陈傅良一事,《宋元学案》中说:“湖湘学者以先生与吴畏斋为第一。南轩卒,其弟子尽归止斋,先生亦受业焉。”[61]当然,就胡大时个人而言,研习事功之学也并非特例,因为除了问学于陈傅良之外,他还曾问学于朱熹与陆九渊,《宋元学案》就说他“又往来于朱子,问难不遗余力”,“最后师象山”[62],也就是说胡大时最后的学术归宿,在于陆九渊的心学,他问学陈傅良也只是某一阶段而言。不过也正因为胡大时在湖湘学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的举动对陈傅良“尽收南轩门人”一事有着重要的影响。
再说之所以陈傅良讲学岳麓书院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是因为陈傅良的事功之学承继于薛季宣等人而又有创新,学术水平颇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湖湘之学除了重视性理之学外,本来就还有着经世的传统,自从胡安国讲春秋学以来,湖湘学者“爱君忧国”,而“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63]。因此,陈傅良所传浙学,能够与湖湘之学颇为合拍,引功利思想入湖湘经世传统,其实也是对湖湘之学的很好的补充。

张栻像 朱熹像
『四、“朱张”传统的确立』
嘉定十五年(1222),朱子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真德秀,以宝谟阁待制兼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在他知潭州期间,对于岳麓书院以及湖湘之学有着极大的推动。特别是对于湖湘学术“朱张”传统的确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真德秀曾多次亲自到岳麓书院,并且主持书院的祭典。在祭祀之中,一方面推崇有功于书院建设的历史人物,如朱洞、周式、刘珙等;另一方面对书院相关湖湘学脉的代表人物大加褒扬:
濓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 生程纯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峰先生胡公、南轩先生张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圣学不明,千有余载,数先生相继而出,遂续孔孟不传之统,可谓盛矣!惟时湖湘渊源最正,盖濓溪之生,实自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 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64]
真德秀指出“惟时湖湘渊源最正”,因为前有周敦颐,再有胡安国、胡宏父子闻道于二程,再后又有张栻、朱熹讲学于此,此数先生相继而出,方才使得孔孟圣学得以传承。此文对湖湘渊源,强调的是张栻与朱熹“二先生”,但张栻排在前面。他还作有《劝学文》也是如此,其中说:“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65]在简要叙述周敦颐与胡安国父子之功绩之后,此文重点对张栻、朱熹二人之于湖湘学术的重要性加以阐明:
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极之士,登门墙承謦亥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他那国所可及。
他指出张栻与朱熹二人之学,其源出于一,也就是都为洛学之后续,而他们自己发明之学又都是集合了湖湘乃至当时学术之大成,所以当时湖湘学派人才辈出。在此文之中,真德秀还指出张栻、朱熹二人之书对于后学的指导意义:
今二先生虽远,所著之书具存,皆学者所当加意。而南轩之《论》《孟》,晦奄之《大学》《中庸》章句式问,《论》《孟》集注,则于学者为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颇闻迩来学子,急于场屋科举之业,往往视为近缓,置不复观。殊不知二先生之书,旁贯群言,博世综务,犹高山巨海,瑰材秘宝,随取随足。得其大者因可以穷天地万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至于文章之妙,浑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仿佛,盖其本身木茂,有不期然而然者。……自今以始,学校痒塾之士,宜先刻意于二先生之书矣。俟其次洽贯通,然后博求。
他认为张栻与朱熹都有《四书》方面的论著,这些论著对于初学者非常重要,可以作为入学的门径、基础。《岳麓志》对真德秀知潭州之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有高度的评价:“尤乐育人才,以周、程、朱、张之学劝勉学子。是的讲学虽废,而教化大行。”虽然真德秀没来得及进行大规模的讲学活动,但是对湖湘学子的劝勉,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
端平元年(1234),另一位朱子后学的代表人物、与真德秀齐名的魏了翁,以资政殿学士知潭州。关于魏了翁,上文讨论张栻对蜀学的影响之时有所提及,他可以说是私淑朱熹、张栻之学而有大成的学者,全祖望指出:“嘉定而后,私淑朱、张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66]他在知潭州期间,曾讲学于岳麓书院,也以朱、张之学劝勉湖湘学子。福建人吕中也说:“岳麓、白鹿书院又得张、朱二先生振之。回视州县之学,不过世俗之文进取之策,其相去岂直千百驿而已哉?”[67]张栻与朱熹讲学于书院,对于当时学风的倡导,确实影响深远。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表示,数据表明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保持稳固。前期出台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正在逐步发挥作用,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开局良好。
调查显示,中青年用户是移动支付的主力,中高年龄段人群使用移动支付的比例也在增加。使用移动支付的人群中,18-40岁人群占比是65.3%,40岁以上的人群占整体的34.2%,比上一年增长5.7个百分点。
对于朱张传统的进一步巩固起到重要作用的还有张栻的侄子张忠恕(字行父,学者称拙斋先生)与张庶(字唏颜)二人。张忠恕早年受学于张栻,嘉定年间讲学于岳麓书院,对于湖湘学子有着重要的影响,全祖望对其评价非常之高:“中兴四大儒之后,先生最有光于世学。”[68]此处的四大儒是指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在他们之后在湖湘地区,张忠恕当有着重要的地位。张栻的另一位侄子张庶,也受学于张栻,在岳麓书院听讲之时,曾任司录,记载了许多张栻讲学的内容。后来他也曾在岳麓书院讲学。张栻的这些弟子或再传弟子继续传承湖湘学脉,并且对朱、张二人大力推崇,从而奠定了朱、张之学在湖湘的正宗地位,这一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之后好几百年。
到了元代,至正二十三年(1286)潭州学正郡人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湖湘学子再次以岳麓山为中心讲学论道。延祐元年(1314)再次大规模重修岳麓书院,发起此次重修、在潭州董理学事的刘安仁,还请了著名理学家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号草庐,抚州豢仁人)撰写了《重建岳麓书院记》、《百泉轩记》以志其事。吴澄《百泉轩记》除了详细记载百泉轩的历史与景色之外,还特别提及“朱张”传统:
朱子元晦,张子敬夫,聚处同游岳麓也,昼而燕坐,夜而栖宿,必于是也。二先生之酷爱是泉也,盖非止于玩物适情而已,逝者于斯夫!不舍昼夜。惟知道者能言之。呜呼!岂凡儒俗士之所得闻哉。[69]
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一文之中,详述了元代重修岳麓书院之经过之后,特别指出周敦颐之于儒学的重要性,更特别强调朱、张岳麓会讲对湖湘学脉的重要意义。他说:
孟子以来,圣学无传况数百年之久。衡岳之灵钟为异人,而有周子生于湖广之道州,亚孔并颜,而接曾子、子思、孟子不传之绪。其源既开,其流逐衍,又百余年而有广汉张子家于潭,新安朱子官于潭。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聚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自此以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也!地以人而重也![70]
在吴澄看来,朱、张会讲之后的岳麓书院已经不是之前的岳麓书院,而成为儒学的圣地。吴澄在此文之中还特别强调了张栻的功绩:“且张子之记尝言当时郡侯所愿望矣,欲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时也,而其要曰仁。”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以“仁”为宗旨而确立“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时”的学术传统,可以说是书院的宝贵财富。
岳麓书院的朱、张传统,在明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弘治七年(1494),长沙府通判任陈钢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七月开工,次年完成。这次重建,陈钢首创朱、张专祠——崇道祠,还有知府杨茂元建尊经阁,井嵌刻“紫阳遗迹”,分麓山讲学、衡岳同游、安抚湖南、谕降硐獠、更建书院、节制虎军,考正礼仪、录旌忠节等八题,每题书年谱之文于首,命工分绘为图,并作赞语于后,特别彰显了朱熹在湖湘的功绩。当时正逢著名诗人李东阳回湘省亲,特别为重建的岳麓书院作记,在叙述此次重修岳麓书院之经过之后,也特别强调了朱、张之传统:
且南轩得衡山胡氏言仁之旨,观所为书院记,亦惓惓以是为辞。晦翁之学,固有大于彼,然亦资而有之。后之学者,曾不逮其万一,而不百倍其功恶可哉?由南轩而企晦翁之学,等而上之,以希所谓古之人者,庶几为兹院之重,以为山川之光,若其程格条绪,则存乎教与学,吾于吾乡大夫士望之矣。[71]
张栻传承的湖湘“言仁之旨”与朱熹之学,已经成为书院教学的重要资源,湖湘后学应当自觉加以继承。之后还有著名的山长陈论,进一步倡导朱张之学。陈论,字思鲁,湖南攸县人。正德三年(1508)任岳麓书院山长。在他所作的《圣学统宗》之中,其中说:
岳麓之兴本于朱张,朱张之学本乎道也。首之以圣学统宗,所以原其相传之有自,又以望后来者于无穷也。嗟夫,斯地昔称小邹鲁矣!当其盛时,产于斯者营道舂陵之间有濂溪周子,黄州程乡有明道、伊川二程子;宦游于斯者,浏阳有龟山杨子,应山有上蔡谢子,衡岳湘潭有武陵胡氏父子,潭州有晦庵朱子、南轩张子,继晦庵来守者又有真西山焉,识者号曰湖南一派,不诬也。慨自朱张没,而孔孟正学之传绝焉。然果终绝乎哉?”[72]
他还指出,岳麓书院的复兴,就是要以承继湖湘的朱张传统为重要使命。此后朱张传统被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学者所重视,直到后来的岳麓书院改制为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任湖南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胡庶华先生作词,并且沿用至今的校歌之中依旧有“承朱张之绪”一句,当是对于朱张传统的一种回响。
『结语』
以张栻为中心,可以很好地把握湖湘学脉,从“胡张”到“朱张”学统的转换,既是湖湘学内部演进的结果,也是朱熹两度讲学以及后来朱子学成为官方认可的学术正统等外部影响的结果,此外还有浙学的影响也值得注意。
就张栻的学术渊源来说,先是通过张浚而承接其忠孝家法以及谯定易学为主的蜀学,再是受学于刘芮与王大宝,然而造就其以性理之学为主体的最终学术形态,最为重要的还是师事于胡宏,正是通过胡安国、胡宏这一脉而承接了渐成规模的湖湘学派。值得注意的是,张栻上述几支师承之中都有一定的洛学因素,成为其后来与朱熹论学的重要基础。还有在朱熹的影响之下,张栻由胡宏《知言》而上溯周敦颐《太极图说》并进行重新解释,种种因缘最终使其成为湖湘学脉之中集大成的人物。
张栻也是多个地域学派交流的关键人物,先是他本人不负众望,讲学于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将湖湘学派发扬光大,不但湖湘一带的学子云集于此,还吸引了许多重要的蜀地学子,通过他们而将其学重新西返,促成了蜀学再盛。张栻待人以诚,与浙学之中的薛季宣、陈傅良等学者也多有交往,特别是陈傅良问学于张栻,后来又到湖南任官,虽不可断言“收尽南轩门人”,但对湖湘学脉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一是向朝廷举荐湖湘学子,一是讲学于岳麓书院,将事功之学传播于湖湘,尤其对胡国安之孙、胡宏之子胡大时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张栻身后,再度梳理湖湘学脉,从而将“胡张”传统转换为“朱张”传统的关键人物则为真德秀,此后接续而弘扬的则还有魏了翁与张忠恕、张庶、陈钢、杨茂元、陈论等人。真德秀曾多次亲自到岳麓书院,并且主持书院的祭典。在祭祀之中,对湖湘学脉的代表人物大加褒扬,“惟时湖湘渊源最正”,前有周敦颐,胡安国、胡宏父子闻道于二程,再有张栻、朱熹讲学于此,此数先生相继而出,方才使得孔孟圣学得以传承。他对张栻、朱熹二人之于湖湘学术的重要性加以阐明,指出二人之学源出于一,都为洛学之后续,而二人自己发明之学又是集合了湖湘以及当时学术之大成。魏了翁在知潭州期间也讲学于岳麓书院,以朱、张之学劝勉湖湘学子。张栻的侄子张忠恕与张庶也曾参与讲学,张栻弟子或再传弟子接续湖湘学脉,也对朱、张二人大力推崇,从而最终奠定了湖湘朱、张之学的正宗地位。
到了元代,吴澄撰写的《重建岳麓书院记》与《百泉轩记》在指出周敦颐之于儒学的重要性之后,特别强调朱、张岳麓会讲的意义,此后的岳麓书院已成为儒学的圣地。明代重修岳麓书院,陈钢首创专祠朱、张的崇道祠,杨茂元建尊经阁井嵌刻“紫阳遗迹”,诗人李东阳为岳麓书院作记,也特别强调了“朱张”传统,后来还有著名山长陈论,进一步倡导以承继湖湘的“朱张”传统为使命。
概言之,作为湖湘学派的中流砥柱,张栻无论为人为学都当之无愧,从“胡张”到“朱张”,湖湘学脉的转换,虽说主要是因为朱子学成为官学,但其中不变的内核还是集湖湘学脉之大成的张栻之学,毕竟在南宋的乾淳年间,湖湘学派在达到了最鼎盛的历史时期,成为当时儒学的第一大学派,并且在与其他地域学术之间的交流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张天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现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朱子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张栻与湖湘文化研究专委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儒学学会理事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子课题等多项课题研究,出版《张履祥与清初学术》《蕺山学派与明清学术转型》等多部学术专著,《祁彪佳日记》《陆陇其全集》等多种古籍整理,曾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五十多篇网络股指配资哪儿好,曾获得浙江省哲社成果奖、湖南省优秀博士论文等奖项。
